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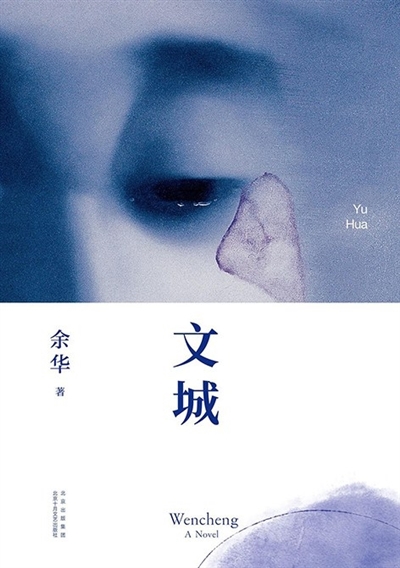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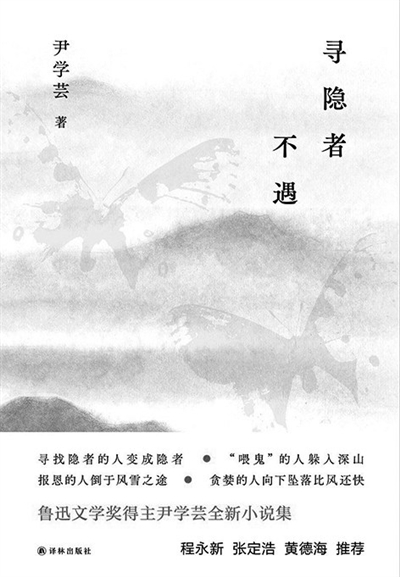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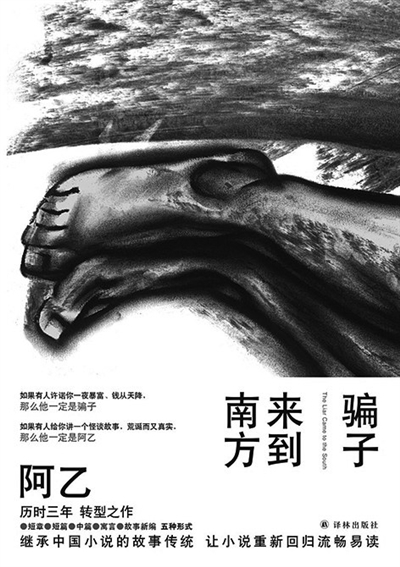

关键词 余华 回望 乡土
■宗城
纵观2021年上半年的小说世界,对世道人心的描摹、对想象力的开拓,以及对当代社会重要议题的回应,成为作家创作中潜藏的三条主线。这其中,既有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深入,也有成名作家、青年作家对先锋技巧的继续琢磨,我们能看到余华、王安忆等已经跻身经典的作家出版新作,也能在茫茫书海中看到陌生却惊喜的面孔,挑战我们的固有成见。
从影响力上来看,2021年小说世界的第一件大事,显然是余华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文城》。这部小说以倒叙、插叙等手法,讲述了北方男人林祥福携女南下寻妻的故事。小说可分为两部分:《文城》和《文城补》,故事背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穿插了对帮会、土匪、军阀、乡绅等人群的描绘,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式写法。最新数据显示,《文城》的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文城》出版后,许多批评家为其献上掌声,但也引起了不小争议。在故事的讲述上,余华设置了一明一暗两个主题。明面主题是林祥福寻找小美的故事,暗面则是对文城的追寻,但文城是什么?它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虚指。“没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背景恰恰是在一个传统礼法崩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人间翻天覆地、信仰重新洗牌的时局,叙述者呼唤文城,想必不只是唱一曲复兴传统的赞歌,而是更深的精神旷野。所谓文城,或许是一个安顿现代人心的地方,但文城永远在路上,不可被到达,它就像是古人常说的“道”,道在顿悟,在求索的路上,而非一个结果。或许,《文城》的质量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它显然是2021文学界的重磅炸弹,值得更多深入的讨论。
除了《文城》,王安忆的新书《一把刀,千个字》也是值得被重点讨论的对象。小说从清袁枚的 “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进入,以纽约法拉盛作为倒叙的开端,以一位淮扬名厨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叙事长度从建国初期到如今,叙事空间跨越了东北、上海、纽约法拉盛、旧金山唐人街等多个地区。
《一把刀,千个字》既是两代人之间的对视,也是对历史废墟的一次勘探与深入。王安忆选择了她熟练的布局严密又暗藏玄机的叙事方式,对历史内部的幽微和“沉默之处”进行了一次正面强攻。在浪漫主义的英雄年代,与市场浮沉的世俗年代的之间,王安忆书写那些与往昔的幽灵搏斗,又在此世疏离仿徨的人。她讲述的既是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也是个体命运所映照的世道更迭与永恒创伤。
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也展现了自己炉火纯青的叙事功力。她在前半部看似涣散的叙事中慢慢蓄力,在法拉盛与过往历史的交替中,使小说有了一种“如歌的行板”似的从容。这部小说既是叙事的美学,也可作为世俗好看的故事,小说对淮扬厨师的描绘、对法拉盛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了人类学研究般的趣味。王安忆令人尊敬的一点,就是她始终在学习,用小说去领略不同行业的风采。她曾说:“许多职业作家到最后常是以写作本身当小说的题材,其实是无奈之举,损失了小说世俗的趣味。行业到精深处就是艺术,器物里面藏着多少故事,而写作者可说是一切行业的门外汉,自己的职业似乎又不能称作行业。我最喜欢听手艺人说话,有一次我送家里一具红木橱去修,木匠行老板一看就说是民国的东西,问从哪里看出,回答榫头,接着告诉各种嵌榫的方法形制,可惜没有基础,完全不能得门而入。”
2021年国内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长河式小说继续涌现,作家们以巨大的魄力,回望了一个时代留下的遗产,其代表作如《有生》《受命》《民谣》。
《有生》是胡学文沉淀多年的史诗之作,2021年中国文学世界不可忽略的一座山峰。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小说的叙事长度从晚清一直到当下,却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它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而是大量利用意识流、倒叙、插叙、闪回的技巧,以伞状结构作为支撑,在祖奶奶这条主线和其余副线的串联之下,赋予了整部小说众声喧哗又苍凉沉郁的质感,为中国的长河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说完《有生》,再说《民谣》。《民谣》是学者王尧沉淀20年写作的回望之书,这是一部“文革”后期少年的“口述”成长史,也是一本写给学者和评论家看的索引式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通过主人公王厚平1972年在码头上的所知所感,展开了一卷长河般的历史叙事。在少年的成长与回望中,王尧同时涉及了革命史和家庭史的断裂和重建,在一种日光流年般的沧桑笔调中,王尧引着读者顺着流水,进入乡土中国的历史深处。
《民谣》的语言有散文和诗的融合质感,小说在一种哀愁、沉郁的口吻中,不疾不徐地展现出一代人心灵史的光亮和暗面。《民谣》的厚重与诗意,也让它在《收获》发表后就引起如潮好评。《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到《民谣》,王尧已获得一个真正有汉语之子的地位。”
(下转第10版) (上接第9版)
今年的一大意外之喜,是长篇小说《受命》。《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他本人说也将是最后一部。这部小说回到了那个天真而感伤的1980年代,通过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场、言说,对北京风物事无巨细地描写,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语调,令哪怕是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读者,也能具体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朝气、理想主义,以及男女之间暧昧和朦胧的情愫。
这是一部迟到二十多年的小说。在《喜剧作家》后记里,止庵曾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作了详细的提纲、人物小传等,并且起名‘神话’。但因为他在外企打工没有时间动笔,一下子就搁置了四分之一世纪。止庵把这部小说称为‘我最后想写的小说’”。(转述自张钊《止庵的〈受命〉,记录时代的腔调》)
后来,这部原名《神话》的小说,改名叫《受命》。取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小说以复仇为引子,还原1980年代北京的生活质感。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一个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间,如何处理羁绊。复仇是引子,背后是绵延无尽的记忆深渊,那些过去,父辈的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所留下的精神负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笔债,又如何坦然地放下过去,面对未来。
止庵怀抱着一种追忆的情绪来写这部小说,不只是对青春时期的追忆,也是对一种日渐逝去的北京文化和精神的追忆。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诚恳,他老老实实地写一个1980年代的故事,一个力求复活那个年代某些侧面的精神品质和物质生活的故事,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虚构,却有非常真实的生活的触感,它流淌着一股真与诚的余味。
中生代作家稳步前进
在成名已久的作家持续创作时,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中生代作家,也在自己的小说道路上稳步前进。朱岳的《脱缰之马》完全打破自我,他的小说仿佛一个又一个分身。朱岳的小说专注于有趣和好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浅薄,而是以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来抵达小说的秘密。而何大草的武侠小说《拳》,以武写文,看似回望武林宗师,其实是在探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用意跟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殊途同归。
在这批作家里,孙频和阿乙也是不满足于自己舒适区的人物。孙频是80后,早期以疼痛文学闻名于小说世界,她对女性身体体验的把握、对于人内心复杂之处的勘测,在《疼》《盐》等多部作品里都已经让读者大开眼界。今年出版的《以鸟兽之名》则是孙频的转型之作,小说收录了孙频最新发表在《收获》等刊物的三部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三部作品主题不同,但都具备一个寻隐的视角,既有在废墟中建造江南园林的神秘人物,也有一桩凶案牵扯出的乡村秘密。孙频书写了一颗颗时代变革中的失落之心,在对古老村落、寂寞行人、当代隐逸者的探寻中,展现出人心的复杂与深邃。
相比孙频,阿乙则是在先锋小说的路上愈发开阔。《骗子来到南方》是他的最新中短篇集,小说由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五个部分组成,是阿乙熔炼先锋气质与县城日常的一部奇绝之作。这部小说集既有同名中篇小说《骗子来到南方》这样运笔细密、气韵充沛,结尾还能别开生面的县城世俗故事,也有《生活风格》这样冷硬又直面人性复杂之处的小说。阿乙小说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真正实践在地式先锋书写,并将史诗风格与世俗生活融汇贯通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深值于中国南方乡土的日常,又具有一种向上拷问生命更高意义的气质。
还有一位作家写作已久,论年岁也是孙频和阿乙的长辈,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却异常生猛,犹如刚刚步入巅峰期的中生代,她就是尹学芸。
《寻隐者不遇》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尹学芸的最新中篇小说集,从基层官员写到市井百姓,从互联网穿梭到寻常巷陌,尹学芸笔法老练、布局沉稳,在不同题材的小说里保持了连贯的水准。在她看似朴拙的文字里藏匿着犀利的笔锋,不紧不慢的叙述中蕴含着小说家对人情世故的深入洞察。同名中篇《寻隐者不遇》如同诗篇,寻隐者不遇隐者而自行隐去;《望湖楼》借民间写官场,勾勒出基层官员和乡镇村民的共生网络;《苹果树》写渡尽劫波的两人心灵却再难相通;《喂鬼》写的则是农村人沉重的命。《收获》主编程永新评价尹学芸,说她:“进入什么都能写、怎么写都不会写坏的境地”。在中篇领域,尹学芸已经是国内一流的小说家。她对世态洞察却并不油滑,在纯文学期刊发表已久但没有那种老态龙钟、拿腔拿调的生硬,正如评论家张定浩所说:“在这些结构纯熟、耐心细密、充满烟火气的故事里,总有一些锋利之物隐伏其中,像一个技艺精良的绣师遗落于枕被中的针,我们猝不及防地被它刺痛,想到那双编织人世温厚的手也曾戳破着人世,或者二者就是一体的。”
在我国港台作家方面,香港作家西西延续了她强健的笔力。西西是当代香港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这部《钦天监》是她的全新历史长篇。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与前作《哨鹿》异曲同工,把明末清初作为背景,以一位供职于清廷钦天监的普通官僚作为中心人物,官僚周若闳的家世沉浮为横面,钦天监的历史脉络为轴,在宛如一幅历史长卷的笔触中描绘中西方文化与视角的差异,以及被政治漩涡裹挟的普通人的命运变迁。
西西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材料组织能力。小说融合了东方占星术、周易、史学与西方天文学、几何、数学、地理学等知识,穿插宫廷奏折、明清笔记、传教士日记、回忆录等材料,内容细密,却并不冗长,作家没有把小说作为一种知识的炫耀术,而是让知识为整个故事服务,借助故事生发出历史思辨和对当下的启示。
西西的《钦天监》是一部反映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社会心理,以及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中如何自处的作品。对于个人在大时代变迁中的无力,作家写得入情入理,读罢令人掩卷叹息。
此外,在现实主义这座高山上,军旅小说、家族小说、乡土小说也有新的收获。它们主要以革命之路、建党建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建设的重要事件为素材,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重大历史题材。例如何建明《雨花台》、石钟山《五湖四海》、刘庆邦《堂叔堂》、王松《暖夏》等。也有作家另辟蹊径,如黄怒波《珠峰海螺》,用长篇小说的体量来写登顶珠峰的故事,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而季宇的《群山呼啸》,写的是清朝末年的家族故事,用小家喻大家,以家族命运来写国事浮沉。邵丽的《金枝》,则是在家族叙事里强调了女性的命运,在几代人的周旋与继承之中,书写中国女性的坚韧。
2021年也是青年作家继续创作实践的一年。在去年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林棹《流溪》、王占黑《小花旦》、金特《冬民》、双翅目《公鸡王子》等惊喜之作后,今年青年作家普遍在把严肃内核与类型叙事相结合,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创作手法,呈现出他们对现实与想象的体会。例如陈思安《体内火焰》、东来《奇迹之年》、沈大成《迷路员》、路魖《角色X》、钱墨痕《俄耳普斯的春天》、程皎旸《危险动物》、张叶《四楼的玻璃柱》等。他们的题材各异,但都在将推想、悬疑、科幻、古典等元素与文体融合,邀请读者走入更富想象力的世界。
还有一路作家则回归到老老实实讲故事的传统。他们继承了契诃夫、巴尔扎克等作家的现实主义笔法,截取城市、乡土社会的侧影,反映若干群体的生活困境与精神状态。其代表如张慧雯的《飞鸟与池鱼》。在这部小说集里,张慧雯展现了一种契诃夫式的分寸感。她的运笔细腻节制,别开生面,流露着异乡者对故土的深情回望。张惠雯是一位创作上极为耐心的作者,她的小说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还乡”传统,致力于书写漂泊于城乡之间、异国与故土之间的人们。在写作县城与还乡者时,张慧雯的笔触尤其老练。如同作家林培源所说:“这些小说里,总有一双善良看待世界的眼,但内里又有张惠雯自身独特的风格和腔调,细腻、内敛,动人处如同一霎那的火光,照耀黑暗。”
葛亮的《瓦猫》以典雅语言,为手艺人立碑,他让过去在文学史上并不显赫的人群,以群像方式出现在小说世界。而一笔一划间,延续了葛亮在《北鸢》《朱雀》中的文字气韵。此外,邓安庆的《永隔一江水》是他目前为止最成熟的创作,书写的是乡土社会的人心世道,留有恻隐之心的余味;乔叶的《朵朵的星》属于儿童文学,是一部关于儿童成长的温暖小说;《我是余欢水》原著作者余耕的新小说集《我是夏始之》,写的是当代社会里的平凡小人物,延续了和余欢水一样的味道。
“你能勘破你自己吗?”作家东西耗时四年,创作出长篇小说《回响》,首发于《人民文学》,出版后得到作家余华、导演陈建斌、评论家孟繁华等名家的推荐。这部作品以悬疑案件为切入口,但它并不只是一部推理爽文,而是在悬疑的外衣下,隐藏着作家对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处灰色地带的勘探。这是一部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也蕴含了诸多推理学和心理学上的知识,写作难度不小,也很考验作家在可读性和严肃性上的平衡。它在类型上属于侦探小说,但仔细琢磨,它其实更像心理小说,它所注重的不是本格推理作品式的手法,而是通过罪案,深入挖掘人的心理。因此,有评论家把该作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韩少功曾说东西的小说:“一个个坚实的细节差不多是呼啦啦喷涌,是话赶话扑面而来,全程紧绷,全程高能,构成了密不透风和高潮迭起的打击力。老把式们才知道这种活儿有多难。这种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是一段岁月深处蕴积和发酵的生命本然。”《回响》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马华文学强势崛起
最后,虽然并不属于国内小说的范畴,但作为华语文学大家庭的一员,马华文学在近年来的强势崛起尤为值得关注。以黄锦树、黎紫书、张贵兴、李永平、贺淑芳为代表的一批马华作家,在文字上展现了自己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想象力。今年值得关注的两本,是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和黎紫书的《流俗地》,它们完全有资格竞争年度最杰出的华语长篇小说。
《野猪渡河》是张贵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红楼梦文学奖的优胜作品。张贵兴把故事放在二战日据时期,日本南侵马来群岛,砂拉越沦陷,22个男人的头颅被砍下,当原住民被恐惧的阴影笼罩时,一只露出獠牙的公猪伸出舌头舔舐死者的血液,正准备与母猪交配。故事就这样在人与物视角交换的叙事中展开,野猪成为窥探人类世界乱象的一个叙事工具。在《野猪渡河》中,张贵兴不但延续了《猴杯》狂暴、骇丽如同雨林藤蔓般疯长的语言,也在对南洋历史的深潜中,书写了“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的叙事质感。小说中人对自我的美化被无情剥夺,人和动物在叙事上近乎平等,张贵兴用雨林的湿热危险与历史的诡谲莫测相结合,在对文本的建构与打破,对叙事视角和时间顺序的打乱和重组中,张贵兴刻画出一个华美地狱般的矛盾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源源不断的性爱、虐杀和权力更替,正因如此,《野猪渡河》超越了普通的伤痕叙事、英雄主义叙事,呈现出历史肌肤上更细致的纹路,更重要的是对人本位的小说传统做出了反思。
《流俗地》则展现了马来西亚市民性的一面,是对马华各民族相处,尤其是女性世界的幽微呈现。黎紫书通过对盲女银霞的命运书写,在革命与流亡、殖民与反抗等传统马华文学叙事路径之外,开拓出新的对马来世界的讲述方式,在她四两拨千斤的语言中,有对马来社会极为精确的写照。
最后,需要致歉的是,笔者已经争取抽出尽量多的时间来阅读作品,但仍感到书海茫茫、无穷无尽。因此,我必须对遗漏的作家说一声抱歉,也希望读者只是把这篇述评作为入门之砖,能够辩证地看待本文存在的不足。
宗城 1997年生人。广东湛江人,小说写作者、文学批评者,曾获广西师大书评奖、香港青年文学奖,作品散见于《广州文艺》《单读》《西湖》《ONE》《SIXTH TONE》《作品》《财新周刊》《新华文摘》等杂志或媒体。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